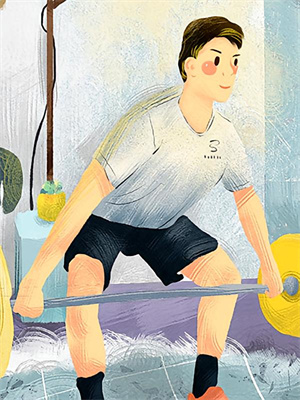简介
小说《寒门青云路:我在大景考状元》的主角是林牧,一个充满魅力的角色。作者“没有笔墨的洲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。如果你喜欢历史脑洞小说,那么这本书将是你的不二之选。目前本书已经连载等你来读!
寒门青云路:我在大景考状元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三月底的汴京县学,午后显得有些慵懒。几株老槐树抽出嫩绿的新叶,阳光透过枝叶洒在青石板上,光影斑驳。明伦堂内隐约传来教谕授课的声音,几个闲散的学子在回廊下低声交谈,或独自捧书默读。
林牧踏入县学大门,门房认得这位新科案首,客气地点了点头,并未多问。他尽量让自己步履显得从容,先是到礼房递了府试报名的最后一份材料——这是早就准备好的,此时递上,只为留下一个确切的行踪记录。管事的书吏笑着恭喜他几句,在簿册上记下时辰。
随后,他沿着回廊缓步走向后院的藏书阁。路上遇到两位相熟的生员,互相拱手见礼。林牧状似随意地提及,午后要去白石书院拜会一位师长,请教府试文章。那两位生员不疑有他,还羡慕他能得到书院讲席的指点。
在藏书阁象征性地借了一本《范文正公集》,林牧再次向门房点头致意,走出了县学。他没有直接前往位于城东的白石书院,而是拐进一条小巷,迅速脱下外面的灰布衣服,露出里面那套半旧的靛蓝生员襕衫。他将灰衣卷起塞进借书的布袋,又将头发重新仔细束好,深吸一口气,调整了面部表情,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正常去赴会的年轻士子,这才快步向城东走去。
白石书院坐落在汴京东郊一片幽静的竹林中,粉墙黛瓦,环境清雅。林牧抵达时,已近申时(下午三点)。书院门口,已停着几辆装饰朴素的马车,显示已有访客先到。门子验看了请柬,恭敬地引他入内。
穿过影壁,是一个开阔的庭院,正中一棵古松虬枝盘结。庭院两侧的厢房隐隐传来辩论之声。门子引着林牧走向正堂,廊下已站了几位同样年轻、穿着生员服饰的学子,正低声交谈,正是今科县试中名列前茅的几位,包括榜眼陈启明、探花吴怀远等人。
见林牧到来,陈启明率先笑着迎上:“林案首来了!我等正在猜你何时会到。” 吴怀远也拱手为礼,态度比县学时亲近不少,毕竟算是“同门”相邀。
林牧压下心中焦虑,一一还礼,笑道:“让诸位久候了。临时去县学办些手续,耽搁了片刻。”
正寒暄间,正堂门开,那位拜访过文华斋的苏慎讲席走了出来,笑容满面:“诸位才俊都已到了,快请进。山长和几位先生已在堂内。”
众人肃整衣冠,随苏慎步入正堂。堂内宽敞明亮,布置简朴,唯墙上挂着几幅山水字画,透出雅致。上首坐着三位老者,正中一位,须发花白,面容清癯,眼神温润而睿智,正是书院山长吴敬亭。左右两位,一位是面容严肃的经学讲席,另一位则是位气质洒然的诗文大家。
林牧随着众人向山长及诸位先生行礼。吴敬亭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,尤其在林牧脸上停留了片刻,微微颔首,却未多言。
众人落座,童子奉上清茶。春讲开始,先由一位讲席就《春秋》中“郑伯克段于鄢”的微言大义做了一番阐发,鞭辟入里,众人听得聚精会神。随后,吴敬亭山长便让在座学子畅所欲言,就府试可能涉及的方向或学问疑难提问交流。
陈启明等人先后发言,或请教经义,或探讨策论写法,气氛渐趋热烈。林牧心神不宁,却不得不强打精神,偶尔插言几句,所言皆中肯要害,引得吴敬亭多看了他几眼。
轮到吴怀远时,他起身向山长和诸位同窗拱手,然后转向林牧,语气诚恳:“林案首,怀远有一事请教。县试策论,案首‘固本待时’之论,高屋建瓴。然学生近日思及北疆实务,如军械改良、边储转运等具体‘固本’之策,常感空有想法,却不知如何切入,方能既切中时弊,又不过于敏感,惹来非议。不知案首对此,可有以教我?”
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巧妙,既捧了林牧,又将话题引向了林牧目前最关切也最危险的领域——军械、边储!林牧心中一凛,怀疑吴怀远是否意有所指,但看对方神色坦荡,似乎只是单纯请教。
堂内安静下来,众人都看向林牧。吴敬亭山长也捻须不语,目光沉静。
林牧知道,这是一个机会,一个或许能将他面临的困境,以学问探讨的方式,隐隐传递出去的窗口。他必须把握分寸。
他略作沉吟,缓缓开口:“吴兄此问,切中肯綮。学生浅见,‘固本’之策,首在‘务实’与‘循序’。譬如军械改良,工匠技艺、物料材质、军中实用,缺一不可。献策者当深察其情,所提之策,需工匠能作,物料易得,兵士善用。若徒有奇思,不切实际,反为空中楼阁。”
他顿了顿,继续道:“至于‘切入’之道,或可先着眼于‘已有之弊,细微之改’。譬如军中旧弩,若射程、力道尚可,唯上弦费力、易损,则可专研省力耐用之法。此等改良,看似细微,却于提升战力有切实之效,且不易触动太大利益,推行阻力或小。待小改见效,根基渐稳,再图更大革新,方为稳妥。此亦‘待时’之一解。”
他没有提任何具体技术,只阐述方法论,既回答了问题,又显得深思熟虑,符合他“沉稳务实”的形象。
吴怀远听罢,若有所思,点头道:“‘已有之弊,细微之改’……案首之言,令学生豁然开朗。不贪大求全,积小胜为大胜,实乃老成谋国之见。”
吴敬亭山长此时终于开口,声音平和却带着穿透力:“林生员所言,甚合‘中庸’之道。过犹不及,革新亦然。然‘细微之改’,亦需有心人察见,有力人推行,有势人庇护。否则,纵有良策,亦恐埋没于尘埃,或夭折于襁褓。” 他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林牧,话中似有深意,“我辈读书人,明理之余,亦需知世情,识时务。譬如一株幼苗,需有沃土、阳光、雨露,更需避开狂风暴雨,方能成长。这‘避’之一字,有时比‘进’更难,也更要紧。”
“避”!林牧心头剧震。吴山长竟用了他从陈大福血书中解读出的同一个字!这是巧合,还是……他强行稳住心神,躬身道:“山长教诲,学生铭记。幼苗生长,确需仰赖诸多因缘庇护。”
话题随后被吴敬亭引开,转向诗文鉴赏。林牧却再也难以完全集中精神,吴山长那番话在他脑中反复回响。这位与父亲可能有旧的山长,是否知道些什么?他的话是泛泛而谈,还是针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有所暗示?
春讲持续了近两个时辰,直至日影西斜。结束后,吴敬亭留下众学子用便饭。席间气氛轻松不少,众人谈笑风生。林牧寻了个机会,落后几步,走到正在廊下独自赏竹的吴敬亭身侧,深深一揖。
“学生林牧,谢山长今日指点迷津。”
吴敬亭转过身,看着他,目光比堂上时更加深邃:“不必多礼。你父亲守诚,当年在府学,虽不善言辞,但为学扎实,性情坚韧。可惜……时运不济。” 他轻轻叹了口气,“你能有今日,他在天之灵,想必欣慰。”
“学生惭愧,对父亲往事所知甚少。”
“往事如烟,不知也罢。”吴敬亭摆摆手,话锋一转,低声道,“你今日所言‘细微之改’,颇见功力。但切记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有些风,起于青萍之末,看似微弱,却能摧折大树。你既已崭露头角,更需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汴京城里,有些地方,有些人,看似与经义文章毫无瓜葛,却能于
他不再犹豫,再次深深一揖,声音压低到只有两人能听见:“山长明鉴。学生确有一事,如鲠在喉。有一至亲长辈,因学生之故,今日忽遭无妄之灾,身陷险地。学生忧心如焚,却投告无门,恐打草惊蛇,反害其性命。不知山长……可有良策指点迷津?” 他没有提陈大福名字,也没说具体地点,只点出“至亲长辈”、“因己之故”、“身陷险地”、“投告无门”,这已足够传达信息。
吴敬亭静静看着他,眼中并无太多惊讶,仿佛早有所料。他沉默片刻,缓缓道:“老夫一介山野闲人,久不问外事。不过,书院有位常年在外采买书籍文具的管事,姓胡,为人机敏,于汴京三教九流都有些门路。他今日恰好回书院述职,此刻应在东厢房账房核账。” 他顿了顿,补充道,“胡管事早年,曾欠你父亲一个人情。”
说完,吴敬亭不再多言,转身缓缓踱步离开,留下林牧独自站在廊下,竹影摇曳,洒在他身上。
东厢房账房!父亲的人情!林牧瞬间明白了吴敬亭的意思。这位胡管事,就是吴敬亭指给他的、可能帮上忙的人!他不敢耽搁,向还在用饭的众人告罪一声,言称身体略有不适,需早些回去休息,便匆匆离席。
按照指引,他很快找到了东厢房的账房。敲门进去,里面一个五十多岁、面容精干、穿着管事服饰的男子正在灯下拨弄算盘,正是胡管事。
“学生林牧,见过胡管事。”林牧行礼。
胡管事抬起头,打量了他几眼,眼中闪过一丝了然,放下算盘:“林公子不必多礼。山长方才已让人传话于我。可是有事需要老朽效劳?” 他开门见山,显然已得了吴敬亭吩咐。
林牧也不再绕弯子,将陈大福可能被“过山虎”手下抓走、以及自己猜测可能关押在“快活林”赌坊后私牢的情况,简略说了一遍,隐去了陈大福调查“军粮”之事,只说是因打探一些旧日恩怨招祸。最后,他恳切道:“胡管事,那位长辈于我恩重如山,学生不能坐视。恳请管事指点一条门路,或能探知他被关押的确切地点,或有办法能与对方说得上话,学生愿倾尽所有,只求保他平安。”
胡管事听完,眉头微皱,手指轻轻敲击桌面:“‘过山虎’……‘快活林’……那是块难啃的骨头。他们与西城兵马司、刑部某些人都有勾连,行事狠辣。直接要人,恐怕不易。” 他沉吟片刻,“不过,他们做的是开门生意,赌坊、妓馆、放贷,图的是财。若你那长辈并非他们必除之而后快的目标,或许……可以用钱试试。”
“需要多少?学生愿筹。”林牧立刻道。
“这不是多少的问题,而是怎么送进去,谁能递话。”胡管事站起身,在房内踱了两步,“这样,我在‘快活林’有个远房表亲,在里头做个不大不小的管事,专管一些杂务,或许能递上话。但这事风险不小,他未必肯干。而且,即便肯干,也需要打点上下。”
“一切但凭胡管事安排!需要多少银钱打点,学生这就去取!”林牧毫不犹豫。徐焕那五十两银票,此刻正好派上用场。
胡管事看了他一眼,点点头:“你倒是爽快。这样,你先回去等消息。我连夜去找我那表亲探探口风。明日辰时,你到西市‘老孙茶楼’二楼雅座‘听雨轩’等我。无论成与不成,我都会给你个信。记住,此事你知我知,绝不可再让第三人知晓,包括山长。我帮你,是还你父亲旧情,也是看在山长面子上,但不会牵扯书院。”
“学生明白!大恩不言谢!”林牧郑重拱手。
离开白石书院时,天色已完全暗下。林牧没有回文华斋,而是绕道去了西市附近,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住下。他心中忐忑,不知胡管事那边能否顺利,更担心陈大福此刻的安危。
这一夜,他几乎未眠。脑中反复思量着各种可能,也回忆着吴敬亭山长的每一句话。父亲早年的一个人情,竟然在此时可能救陈大福一命,这世事机缘,实在难测。他也更加确信,自己正被一张越来越复杂的网包裹着,而网的中心,似乎总与“军粮”二字隐隐相连。
次日辰时,林牧准时来到“老孙茶楼”的“听雨轩”。胡管事已先到了,面前摆着一壶茶,两个杯子。
见林牧进来,胡管事示意他坐下,低声道:“打听清楚了。人确实在‘快活林’后头的私牢里,受了些皮肉之苦,但暂无性命之忧。抓他,是因为他前几天四处打听‘快活林’年前几笔大额银钱进出,尤其是与北边来的客商的交易,触了他们的忌讳。”
北边来的客商!林牧心中又是一紧。这更印证了与军粮案的关联!
“我那表亲说,对方并非一定要他的命,主要是想弄清他背后是谁指使,目的何在。现在还没问出什么。若我们能给出一个合理的‘解释’,并奉上一笔‘压惊钱’,或许能将人赎出来。”
“合理的解释?”林牧皱眉。
“对。比如,就说这老乞丐是替你打听当年你家一笔旧债的下落,无意中冒犯了他们。你作为他的雇主,愿意赔礼道歉,并保证他不再多事。”胡管事道,“这个说法,既解释了老乞丐的行为,又把你推到前面,但你的身份是案首生员,他们多少会有些顾忌,不会轻易动你,反而可能顺水推舟,拿钱了事。”
这主意不错,既能救人,又能将陈大福的私自调查定性为“替主家办事”,避免牵扯出更深的东西。林牧点头:“就依管事所言。需要多少‘压惊钱’?”
胡管事伸出三根手指:“三百两。其中二百两是给‘过山虎’的,五十两打点牢头和看守,另外五十两……是给我那表亲的跑腿费和封口费。”
三百两!这远远超出了林牧的承受能力。徐焕给的五十两加上他之前积蓄,也不过六七十两。但他没有丝毫犹豫:“好!三百两!请管事稍候,我这就去取钱!一个时辰内必回!”
他匆匆离开茶楼,先回到昨夜住宿的小客栈,取出贴身藏着的五十两银票和十几两碎银。然后,他快步走向文华斋。他知道张掌柜或许能凑出一些,但远远不够。他心中已有了一个冒险的打算——动用徐焕赠银中剩余的部分,以及……或许可以暂时“借用”文华斋账上的一些活钱,立下字据,日后加倍偿还。
然而,当他走到离文华斋还有一条街时,却猛地停住了脚步。
文华斋门口,竟然围着一群人,指指点点。两个穿着刑部公服的差役,正站在门口,与一脸焦急的张掌柜说着什么。旁边,还站着那个面熟的黄脸差头王敢!
林牧心头一沉,立刻闪身躲进旁边一条窄巷。文华斋也被找上门了!是因为自己昨天匆匆离开,引起了怀疑?还是对方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,干脆直接对文华斋施压,想逼自己现身?
他背靠冰冷的墙壁,感到一阵寒意。陈大福还等着三百两救命钱,文华斋又遭围困……自己此刻若现身,不但救不了人,恐怕连自身都难保。
怎么办?
他脑中飞速旋转。胡管事那边等不起,必须尽快拿到钱。文华斋不能回,张掌柜自身难保。徐焕?不能找。郑怀安?远水难救近火。
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,目光忽然瞥见巷子对面一家当铺的招牌。他摸了摸怀中,除了银票碎银,只有那支韩庸赠的狼毫笔,那方周文渊赠的古砚他没带在身上,徐焕送的钢胚镇纸也留在了文华斋密室……
等等!他忽然想起昨夜藏匿小包��蔽夹墙,或许还没被发现?
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形。他看了看天色,咬了咬牙,转身,绕向文华斋后巷的方向。
他必须赌一把,在差役发现那个夹墙之前,拿到镯子,凑足三百两,救出陈大福!至于之后如何应对文华斋的麻烦…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春日的阳光依旧明媚,但林牧却感到前路一片昏暗。这汴京城,对他而言,正变得越来越凶险莫测。裹时,似乎将母亲早年给父亲绣的一个荷包也一并塞了进去,那荷包里,好像有母亲的一对陪嫁银镯子!虽不贵重,但或许能当些钱!文华斋虽被盯�无声处,决人生死。”
这话几乎是明示了!林牧心脏狂跳,他几乎可以确定,吴敬亭知道陈大福的事,或者至少知道他被卷入某种与市井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