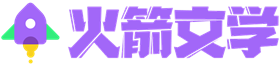简介
《谍影沉城:1941上海暗战》是由作者“喜欢姜荆叶的幽若谷 ”创作编写的一本完结抗战谍战类型小说,沈砚陈峰是这本小说的主角,这本书已更新116640字。
谍影沉城:1941上海暗战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第12章:军火截击
1941年4月13日,上海法租界的安全屋里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只留一盏煤油灯,在桌上投下昏黄的光晕。沈砚之、陈峰和苏清媛围坐在桌旁,桌上摊着一张上海到太原的简易地图,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关键站点——南京、徐州、郑州。
“郑州郊外的‘马家河铁路桥’是最佳设伏点。”沈砚之指着地图上的郑州段,指尖划过铁路桥的标记,“这座桥是日军运输的必经之路,桥身长五十米,下面是湍急的马家河,列车一旦坠入,日军很难快速救援;而且桥两侧有茂密的杨树林,便于隐藏和撤离。”
陈峰点了点头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,展开是日军列车的时刻表:“军统线人查到,这批军火列车是蒸汽机车,挂着十二节车厢,预计下周三上午九点左右经过马家河桥,车速会放慢到每小时二十公里——过桥时需要减速,这是我们的机会。”
苏清媛坐在一旁,手里拿着一本急救手册,正在上面标注重点:“我会准备足够的止血带、磺胺粉和吗啡,战斗中肯定有伤员,得确保能及时处理。另外,我建议提前在桥附近的树林里搭一个临时救护点,离战场五十米左右,既安全又能快速接应伤员。”
三人商量到深夜,最终确定计划:由沈砚之写加密信,详细说明列车时间、路线和设伏点,交由地下党交通员“小吴”送往郑州——小吴是个十六岁的少年,平时以卖报纸为掩护,多次往返上海与根据地,从未出过差错。
沈砚之握着笔,在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小字,每个字都用了地下党专用的密码——比如“粮食”代表军火,“周三赶集”代表列车经过时间,“去舅家送米”代表设伏马家河桥。写完后,他把纸条折成指甲盖大小,塞进一个空心的毛笔杆里,再把毛笔交给小吴:“到了郑州,找‘红星粮店’的王老板,就说‘上海来的亲戚,送米票’,他会带你见游击队的人。路上遇到检查,就说毛笔是给私塾先生送的,千万别慌。”
小吴接过毛笔,小心翼翼地插进布包里,用力点头:“沈大哥放心,我一定送到!”他趁着夜色,从安全屋的后门溜出去,很快消失在巷子里——从上海到郑州,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,还要穿过日军的三道关卡,这一路,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
接下来的三天,沈砚之等人一边等待消息,一边做着出发前的准备。陈峰从军统仓库里调来两把狙击枪和十颗手榴弹,分给沈砚之和自己;苏清媛则把急救用品打包成两个帆布包,里面除了药品,还装了几件干净的纱布和一件备用的白大褂——万一救护点被发现,白大褂或许能成为掩护。
出发前一天晚上,沈砚之回到郊区的联络点,见了若涵。若涵正坐在灯下,给哥哥缝补长衫上的破洞,桌上放着一个布包,里面是她提前烙好的烧饼,还裹着油纸,防止受潮。“哥,路上吃,比火车上的窝头好吃。”若涵把布包递给沈砚之,眼神里满是担忧,“到了郑州,一定要小心,有事就给我发暗号,我会跟苏姐姐的人对接。”
“放心吧,哥很快就回来。”沈砚之摸了摸妹妹的头,心里一阵温暖——自从母亲去世后,若涵就成了他唯一的牵挂,“上海这边有陈峰的人盯着,你别出门太勤,按时去书局上班,别让松井的人起疑心。”
4月17日清晨,沈砚之、苏清媛和陈峰,带着两名军统特工,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,混在火车站的人群中,登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。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,大多是逃难的百姓,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。沈砚之把狙击枪拆成零件,藏在一个装农具的麻袋里,苏清媛则把急救包放在脚边,紧紧盯着——火车每到一个站点,都会有日军检查,他们必须时刻警惕。
果然,火车到达徐州站时,几名日军士兵登上车厢,逐个检查乘客的行李。“打开!都打开!”一个日军士兵用枪指着沈砚之脚边的麻袋,眼神凶狠。沈砚之刚要开口,陈峰突然上前一步,递过一包“哈德门”香烟,用流利的日语说:“太君,这是给老家亲戚带的农具,没什么值钱东西,您辛苦了。”
日军士兵接过香烟,拆开抽了一根,瞥了眼麻袋里的农具零件,没再多问,转身去了下一节车厢。沈砚之松了口气,悄悄对陈峰点了点头——还好有他在,不然这次检查恐怕很难过关。
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,火车终于到达郑州。沈砚之等人按照约定,在“红星粮店”见到了王老板。王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,脸上满是皱纹,他把众人带到粮店后院,掀开地窖的盖子:“跟我来,李队长在下面等你们。”
地窖里空间不大,却挤满了人,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高大的汉子正站在地图前,指挥队员们标注位置——正是郑州游击队队长李刚。他看到沈砚之等人,立刻迎了上来,用力握住沈砚之的手:“沈同志,可把你们盼来了!小吴已经把信送到,我们早就开始准备了!”
李刚的手很粗糙,掌心全是老茧,那是常年握枪、种地留下的痕迹。他指着地图上的马家河桥,兴奋地说:“我们在桥两侧的杨树林里埋了二十公斤炸药,连接了导火索,只要按动引爆器,保证能把桥炸塌!另外,我们还安排了十个队员,埋伏在桥北边的山坡上,负责拦截逃跑的日军。”
沈砚之凑到地图前,仔细看了看炸药的埋设位置,点了点头:“李队长考虑得很周全。这样,战斗开始后,我和陈峰带着他的人,用狙击枪压制日军的火力;游击队的同志负责引爆炸药和正面冲锋;清媛在树林里的临时救护点待命,随时救治伤员。”
接下来的两天,众人一起完善设伏计划。沈砚之带着陈峰和两名军统特工,去马家河桥附近勘察地形,确定狙击点——他选了一棵粗壮的老杨树,树干足够粗,能挡住子弹,树顶的枝桠茂密,便于隐藏。陈峰则在另一棵树上设了第二个狙击点,两人约定,以三声鸟叫为信号,同时开枪打击日军的指挥官。
苏清媛则在救护点忙碌着,她把带来的药品分类摆放,还教游击队的卫生员怎么使用吗啡和磺胺粉:“遇到腿伤、胳膊伤的,先止血,用止血带绑在伤口上方五厘米处,别太紧,能伸进一根手指就行;要是腹部受伤,别轻易移动,用纱布按住伤口,等我来处理。”卫生员是个十八岁的姑娘,叫小敏,学得很认真,一边记一边点头,手里的笔记本很快写满了字。
4月20日,也就是计划中的“截击日”,天还没亮,队员们就悄悄进入了埋伏点。沈砚之趴在老杨树上,调整着狙击枪的瞄准镜,镜头里能清晰地看到马家河桥的栏杆——那是日军列车必经的位置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烧饼,那是若涵做的,还带着淡淡的麦香,心里瞬间充满了力量。
上午八点五十分,远处传来“呜——”的汽笛声,蒸汽机车的烟囱冒着黑烟,慢慢出现在视野里。列车的车头是黑色的,后面挂着十二节绿色的车厢,车厢上用白色的油漆写着“粮食”二字,跟佐藤说的一模一样。
“来了!”李刚趴在桥边的土坡上,压低声音喊道,手里紧紧握着引爆器。队员们立刻屏住呼吸,眼睛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列车。
列车的速度渐渐放慢,车头刚踏上马家河桥,李刚猛地按下引爆器:“引爆!”
“轰——”一声巨响,地动山摇,桥中间的桥段瞬间塌了下去,钢筋和水泥块飞溅,蒸汽机车失去平衡,“哐当”一声掉进河里,溅起巨大的水花。后面的几节车厢也跟着脱轨,有的翻倒在河边,有的悬在断桥的边缘,车厢里的军火箱掉出来,摔在地上发出“砰砰”的声响。
“冲啊!”李刚大喊一声,从土坡上跳起来,带着游击队的队员冲了上去。日军士兵从翻倒的车厢里爬出来,有的受伤了,有的还在顽抗,举着枪朝队员们射击。
沈砚之通过狙击镜,看到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日军,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场,嘴里还大喊着指挥士兵。他深吸一口气,调整呼吸,手指扣动扳机——“砰!”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日军军官的头部,军官应声倒下。
陈峰也开枪了,他瞄准了一个正在扔手榴弹的日军士兵,子弹击中了士兵的肩膀,手榴弹掉在地上,炸伤了旁边的几个日军。两名军统特工则从侧面绕过去,用冲锋枪扫射,日军的火力瞬间被压制。
苏清媛的救护点里,小敏正焦急地等待着。很快,一个游击队队员被抬了过来,他的左腿被子弹击中,鲜血直流。“苏医生!快!”抬担架的队员大喊。苏清媛立刻冲过去,蹲下身子,快速解开队员的裤腿,用剪刀剪开伤口周围的裤子,发现子弹卡在了骨头里。“按住他!”苏清媛对小敏说,一边用镊子夹住子弹,用力拔了出来,然后撒上磺胺粉,用纱布紧紧包扎好,“好了,别乱动,等战斗结束送你去后方医院。”
战斗进行得很激烈,日军虽然人数不多,但装备精良,顽强抵抗。有个年轻的游击队队员,刚冲上去就被子弹擦伤了胳膊,他咬着牙,继续往前冲,李刚看到了,大喊:“小王!回来包扎!别硬撑!”小王却摇了摇头,举着枪朝日军射击:“队长,我没事!不把这些鬼子打跑,我不包扎!”
沈砚之看着眼前的场景,心里一阵感动——这些队员大多是农民,没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,却有着最坚定的信念。他再次扣动扳机,又一个日军士兵倒下。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,日军大部分被歼灭,剩下的几个士兵见势不妙,沿着河边逃跑了。队员们欢呼着冲过去,有的检查翻倒的车厢,有的收缴日军的枪支,还有的在河边打捞掉进水里的军火箱。
“沈同志,你看!”李刚拿着一个被炸破的军火箱跑过来,里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,“这些军火,足够我们装备一个连了!”
沈砚之笑着点头,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他走到临时救护点,苏清媛正在给最后一个伤员包扎伤口,额头上满是汗水,却笑得很开心:“还好,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,休息几天就能恢复。”
陈峰站在断桥边,看着燃烧的车厢,嘴角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他走到沈砚之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沈兄,这次干得不错。要是以后还有这样的合作机会,我还跟你一起干。”
夕阳西下,马家河的水面被染成了金色。队员们扛着缴获的枪支,抬着伤员,朝着营地走去。李刚握着沈砚之的手,用力晃了晃:“沈同志,谢谢你们!这次截击成功,不仅毁了日军的军火,还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,以后他们再想往华北运军火,就得掂量掂量!”
“这是我们共同的功劳。”沈砚之看着身边的队员们,看着远处的杨树林,心里清楚——只要国共合作,只要老百姓支持,只要每个人都为抗日出一份力,就一定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,一定能迎来真正的和平。
离开郑州前,沈砚之给若涵发了一封加密电报,只有短短一句:“米已送到舅家,收成很好。”他知道,妹妹看到这句话,一定会放心——这不仅是报平安,更是在告诉她,他们又打赢了一场仗,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