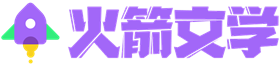期末的望溪教学点,静得能听见风擦过树叶的声响。孩子们伏在课桌上写作业,笔尖划过纸页的“沙沙”声,混着窗外麻雀的啾鸣,裹着午后的阳光漫进教室。林砚坐在隔壁的小办公室里,桌上摊着一摞期末成绩单,最上面那张是陈冬的——语文从开学的五十六分,追到了七十三分,作文纸的边角被孩子用铅笔描了圈,最后一段写着:“林老师的手套很暖和,套在手上,像妈妈的手裹着我。”
林砚捏着红笔,笔尖悬在这句话旁,正要写下“这双手会一直陪着你”,办公桌上那部带天线的老式座机突然响了。铃声尖锐,在安静的屋里炸开来,惊得他手一抖,红墨水在纸页上晕出个小小的墨点,刚好落在“妈妈的手”那几个字旁边,像滴没忍住的泪。
“小林,是我。”听筒里传来王校长的声音,混着中心校操场上的广播声,“中心校财务室缺个踏实人,你是师范生,又细心,下学期调过去做会计。明天上午来中心校办手续,别迟到。”
林砚握着听筒的手猛地收紧,指节泛白。校长的声音干脆利落,没有半句商量的余地,像块石头砸进他心里,溅起的乱绪瞬间淹没了所有声响——窗外的雀鸣、教室里的笔尖声,全都淡了,只剩听筒里残留的“嗡嗡”声,在耳边绕个不停。他张了张嘴,想问“能不能再考虑考虑”,可话到喉咙口,却像被什么堵住,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不知愣了多久,他才缓缓挂了电话。听筒放回座机时,指尖还在抖,不小心碰掉了桌角的搪瓷杯——那是李老师送他的,杯身上印着朵褪色的荷花。半杯凉白开“哗啦”洒在成绩单上,陈冬的名字被水浸得发皱,那个晕开的墨点顺着水痕往下爬,把“七十三分”的“三”字晕成了模糊的一团。林砚慌得伸手去擦,粗糙的纸页被指尖蹭得起了毛,墨渍却越擦越花,像把他心里的乱,全擦在了那张薄薄的纸上。
他撑着桌子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午后的阳光斜斜落在操场上,陈冬正和两个小同学追着跑,怀里抱着个布包,跑起来时布包颠颠的,像是藏着什么宝贝。跑过操场中央时,他忽然停下来,蹲在地上扒拉泥土——那是之前他们约定种向日葵的地方,孩子大概是在模仿翻土,手指插进松松软软的泥里,把一颗小石子埋了进去,嘴里还念叨着什么,虽然听不清,却能看见他嘴角翘着,连阳光落在发梢上,都像是镀了层金粉。
林砚的目光挪回教室,黑板上还留着元旦时陈冬画的画。孩子们舍不得擦,每天课间都会用粉笔描一遍:太阳的金边被描得更亮了,“我们的家”四个字的笔画被填得满满当当,连画里林砚的蓝外套,都被人补了道粉笔灰的边。有个低年级的小丫头正踮着脚,用粉笔画着画里小人的手,大概是想让他们拉得更紧些。
他轻轻推开门,走到教室门口。孩子们听见动静,抬头看了他一眼,又低下头写作业,只有陈冬从座位上探了探脑袋,眼睛亮晶晶的,像藏着两颗小太阳。林砚靠着门框站了会儿,目光扫过课桌上的作业本:有的本子封面掉了,用线缝了两圈;有的字迹歪扭,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;最前排的桌肚里,还放着个用树枝编的小篮子,是孩子们上次上山摘野果时,特意给他留的。
放学铃响时,铃声撞碎了屋里的安静。孩子们瞬间雀跃起来,收拾书包的声响、互相喊着回家的声音,把教学点的静意冲得干干净净。陈冬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,第一个跑到林砚身边,仰着头,把怀里的布包递过来:“林老师,你看。”
布包是用旧衣服缝的,上面还沾着点泥土。陈冬小心翼翼地打开,里面是小半袋葵花籽,颗颗饱满,有的还带着点晒干的花瓣碎渣。“舅公帮我留的,”他声音里带着雀跃,指尖轻轻拨弄着葵花籽,“他说这是去年收的最好的籽,春天种下去,肯定能长出大向日葵,比黑板上画的还高。”
林砚蹲下来,视线刚好和陈冬平齐。孩子的脸颊被风吹得红扑扑的,鼻尖上还沾着点粉笔灰——大概是课间描黑板时蹭的。他的目光落在陈冬的袖口上,灰色的旧手套套在小手上,手腕处那圈他缝的松紧带,洗得有些发白,却依旧紧紧贴着小臂,没像之前那样往下滑。
忽然想起缝手套的那天,他的针尖戳到指腹,陈冬凑过来轻轻吹着伤口,眼里满是慌张;想起画黑板报时,孩子攥着断粉笔,在气球下面补画气泡的认真;想起元旦那天,他把皱巴巴的糖塞进自己手里,说“老师,甜的”。这些细碎的画面像潮水似的涌上来,堵得他喉咙发紧。
“林老师,明年真的种向日葵吗?”陈冬见他没说话,又追问了一句,指尖攥着布包的系带,微微用力,把系带攥出了道褶子。他的眼睛里满是期待,像在等一个能照亮整个冬天的承诺。
林砚抬起手,摸了摸他的头,指尖蹭过他额前的碎发,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传到心里。他想说“可能不行了”,想说“老师要去别的地方了”,可话到嘴边,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看着孩子眼里的光,想起那张写着“像妈妈的手”的作文纸,想起操场上被埋起来的小石子,最终只是点了点头,声音轻得像怕惊碎什么:“嗯,种。”
陈冬笑了,眼睛弯成了月牙,把布包往怀里一抱,转身就往校门口跑,还不忘回头喊:“林老师再见!我会好好收着葵花籽的!”他的背影蹦蹦跳跳,融进山间的暮色里,书包带在背后晃着,像只展翅的小雀。
林砚站在原地,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山路拐角,才缓缓直起身。风从操场吹过来,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,落在黑板前的空地上——那是陈冬刚才埋石子的地方,泥土被翻得松松的,还留着孩子的小脚印。
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。夕阳透过窗户斜进来,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林砚走到桌前,从棉袄内袋里掏出颗裹着透明糖纸的水果糖——是元旦那天陈冬塞给他的。糖纸早已被他攥得发皱,边角磨出了毛边,内侧还沾着点淡黄色的粉笔灰,是孩子揣在口袋里时蹭上的。他指尖摩挲着糖纸,摸到边角有个极小的折痕,想来是陈冬在口袋里反复攥着玩时留下的。
他把糖凑到鼻尖,隐约能闻到淡淡的橘子味,像那天傍晚车把上野菊的香,像孩子笑起来时眼里的光。他一直没舍得拆这颗糖,总觉得拆了,就像把那天的暖、孩子的期待,都变成了转瞬即逝的甜。可现在,指尖攥着糖,耳边又响起王校长的话,眼前却全是陈冬画里的太阳、孩子们追跑时的笑脸、六人围炉喝姜茶时,灯笼里晃悠的烛光。
他拉开抽屉,里面放着本泛黄的教案本,夹着陈冬的作文、画着向日葵的纸条,还有一张他偷偷拓下来的黑板报——用白纸覆在黑板上,用铅笔轻轻涂,把“我们的家”四个字和那些挤在一起的小人,拓得模模糊糊的。他把教案本摊开,从笔筒里倒出三截粉笔头:一截是画黑板报剩下的黄粉笔,一截是陈冬塞给他的断粉笔,还有一截是今天描黑板时,孩子递给他的白粉笔。三截粉笔头滚落在拓片上,刚好停在“家”字的“宀”下面,像三颗紧紧挨着的小石子。
窗外的风又起了,吹得窗棂“吱呀”响。林砚走到窗边,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。山尖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,像陈冬画里的太阳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来教学点的那天,摩托车在山路上打滑,他连人带车摔在泥里,毕业证从包里掉出来,沾了满满一身泥点。那时候他还迷茫,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山坳里待下去,不知道这份乡村教育的苦,自己能不能扛住。
可现在,看着操场上陈冬埋石子的小土坑,看着教室里被描了又描的黑板画,看着桌肚里那个树枝编的小篮子,他忽然懂了——原来短短半年,那些摔在泥里的狼狈,那些深夜备课的疲惫,早就被孩子们的笑脸、同事们的帮扶、家长们递来的红薯和腌菜,酿成了甜。这山坳里的教学点,早已不是一个工作的地方,而是藏着他无数牵挂的家。
他把那颗没拆的糖,轻轻放进教案本里,压在陈冬的作文纸下面。糖纸透过薄薄的纸页,印出个小小的轮廓,像颗藏在文字里的小太阳。夕阳渐渐沉下去,教室里的黑板画被暮色染得温柔,“我们的家”四个字,在昏暗中依旧清晰。
林砚坐在桌前,没开灯。窗外的月光慢慢爬进来,落在他的手背上。他想起陈冬怀里的葵花籽,想起孩子眼里的期待,想起那句“林老师的手套很暖和”,忽然觉得,明天去中心校办手续的脚步,变得格外沉重。
这一夜,教学点的小办公室里,亮了很久的灯。桌上的教案本摊开着,三截粉笔头并排放在“我们的家”拓片旁,那颗裹着皱糖纸的水果糖,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——像个没说出口的约定,像份沉甸甸的牵挂,更像他心里,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,那句“我舍不得走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