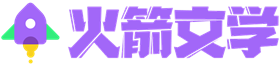老郎中离去后,秦述胸腔里那点灼热并未冷却,反而燃烧得更烈。药性、清补、入方……这些字眼在他脑中反复回响,为他手中的“白玉粉”勾勒出一个远超糊口的、更具价值的未来。
但老郎中也说了,“若处理得法,粉质再澄澈些,性味再平和些”。
眼下他做出的粉,虽能饱腹,却仍带着些许灰扑扑的色泽和极细微的涩味,离“澄净”、“平和”相去甚远。这或许糊弄王婶、搪塞赵四足够,但若想真正将其价值提升,甚至作为能与李瘸子周旋的筹码,还差得远。
必须改进。在现有的粗陋条件下,榨取出极限的纯度。
夜色深沉,他却毫无睡意。将灶膛里将熄未熄的火苗重新引燃,添上几根耐烧的硬柴,让火光成为他挑夜奋战的眼睛。
他首先盯着的是过滤环节。之前用的破麻布和丫丫编的草网,只能滤去粗大的渣滓,更细微的纤维颗粒依旧混在浆液中,这是粉质不够洁白的主要原因。
他需要更细的过滤介质。
秦述在昏暗的屋里四处搜寻。目光掠过墙角堆放的干燥茅草,摇摇头;掠过一件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,布料太过稀疏……最后,他的视线定格在炕席角落一件丫丫小时候用过的、洗得发白几乎透明的旧襁褓布上。
那是极细软的棉布,经纬稀疏却均匀,因为过于老旧,纤维几乎绵软欲化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它裁剪下一大块,又找来两根光滑的细树枝,将布的四角绑住,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悬吊式滤袋。
他将葛根浆倒入这个新滤袋中,任由其自然缓慢地渗滤。速度比之前慢了许多,但底下承接的木桶里,汇聚的浆液肉眼可见地变得清澈了不少,悬浮的细微杂质大多被阻挡在了布囊之内。
第一步,成了!
接着是沉淀。原有的静置沉淀法耗时漫长,且沉淀物分层不够彻底,上层清液总有些浑浊。
秦述想起老郎中提及的“性味平和”。葛根性寒,或许需要一点中和?他并非医者,不懂药性相生相克,但他知道一点朴素的道理——反复淘洗能去除涩味。
他尝试着将初步沉淀后撇去上层清液的湿粉膏,重新加入少量清水,搅拌成浆,再次倒入细布滤袋中过滤、沉淀。如此重复了三次。
每一次重复,都意味着时间和人力的消耗,但效果也是显著的。得到的湿粉膏,颜色愈发白皙,凑近了闻,那股属于植物的生涩气味也几乎淡不可闻,只余下一种极清淡的、近乎虚无的淀粉香气。
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秦述看着眼前一小碗经过三次淘洗沉淀、最后用干净布巾吸去多余水分后得到的干爽粉状物。
它呈现出一种柔和细腻的洁白,在熹微的晨光下,仿佛自带莹润的光泽。用手指捻开,质地细腻滑润,毫无颗粒感。放入口中一点点,几乎尝不到任何异味,只有纯粹的、温顺的淀粉甘甜在舌尖慢慢化开。
这才是真正的“白玉粉”!
与此相比,之前做出的那些,只能算是“灰扑扑的救急口粮”。
秦恒揉着眼睛从屋里出来,看到哥哥通红的双眼和碗里那撮雪白得不似凡物的粉,惊得张大了嘴巴:“哥……这,这是……”
“嗯,还是葛根粉。”秦述的声音因熬夜而沙哑,却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,“我们得想办法,都做成这样的。”
代价是巨大的。近三分之一的葛根原料在反复的淘洗过滤中损耗掉了,得到的高品质粉数量锐减。而且极其耗费时间和人力。
但这值得。唯有提升品质,才能提升价值,才可能在那场注定到来的交锋中,拥有一丝谈话的资本。
丫丫也醒了,趴在门边,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那碗白粉,小声说:“白……像雪……”
秦述将小碗递到她面前,丫丫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沾了一点,放进嘴里,然后眼睛弯成了月牙:“甜……”
秦述摸了摸她的头,对秦恒道:“以后我们分两批做。一批快的,粗做,咱们自己吃,顶饿。一批慢的,细做,就像这样,攒起来。”
他需要数量来维持生存,也需要质量来换取生机。
晨光彻底照亮了小院,新的劳作日开始了。但秦述的心境已有所不同。
他手中握着的,不再仅仅是食物,而是经过淬炼的、蕴含着新可能的——希望。
尽管这希望,依旧纤细如丝,悬于深渊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