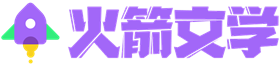北方的夜,黑得早,也黑得透彻。农场亮起稀疏的灯火,更衬得这片废弃的白桦林边缘荒凉死寂。风声穿过光秃秃的枝桠,发出呜咽般的怪响。
林晚拖着行李箱,躲在树林的阴影里,心脏在胸腔里擂鼓。进,还是不进?那个老人的话像魔咒一样在她脑子里盘旋——“死过人”、“不吉利”、“旧伤复发,好几天才被发现”……每一个词都让她毛骨悚然。
可那个军绿色的铁皮柜子,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。一种可怕的、近乎偏执的直觉告诉她,那里面藏着东西。可能与陆沉戈有关,可能与那个矛盾的传闻有关,可能与她这半生都无法安放的愧疚与追寻有关。
她不能再等了。三十年的沉默已经足够漫长。无论里面是真相还是更深的痛苦,她都必须面对。
她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,借着月光,再次走到那扇低矮的破窗前。她先是试着用力推了推那扇朽坏的窗户,纹丝不动,似乎从里面也被什么东西卡死了。她又捡起一块石头,想砸开更大的缺口,又怕动静太大引来农场的人。
最终,她选择了一个最笨拙也最安静的方法——爬。
她将行李箱放在窗下,踩着箱子,试图从那狭窄的破洞里钻进去。洞口很小,边缘还有尖锐的木茬。她不顾一切地用力,衣服被刮破了,手臂和腰侧传来火辣辣的刺痛感,但她咬着牙,一点一点,艰难地挤了进去。
“噗通”一声,她重重摔落在屋子内部的地面上,激起一片灰尘。呛得她连连咳嗽,眼泪都出来了。
屋里一片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只有破窗透进的微弱月光,勉强勾勒出堆叠杂物的模糊轮廓,影影绰绰,如同鬼魅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尘土、霉烂和一种难以言喻的、陈旧的腐败气味。
她摸出手机,打开手电筒功能。光柱划破黑暗,照亮了眼前的景象。
这里果然是个废弃的杂物间。堆满了缺腿的桌椅、破损的农具、散架的箩筐、还有一堆看不清内容的麻袋,上面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。
她的心沉了下去。在这样的地方,真的能找到什么吗?
她用手电光仔细扫射,寻找那个记忆中的军绿色铁皮柜。光线掠过角落,定格!
它果然在那里!比记忆中更旧,锈迹斑斑,绿色漆皮大面积剥落,但款式没错!就是那种部队里常见用来存放文件档案的柜子!
柜门上挂着一把同样锈蚀严重的挂锁。
林晚的心跳再次加速。她走过去,试着拽了拽那把锁,纹丝不动。她又环顾四周,想找找有没有称手的工具。
光线扫过柜子旁边的地面时,她猛地顿住了。
那里,在一堆烂麻袋后面,似乎……有一张简易的行军床的轮廓?床上似乎还堆着些东西,盖着一块肮脏不堪的苦布。
一个可怕的联想窜入脑海——那个老人说的,“死过人”、“窝在这屋里”……
她强忍着恐惧,慢慢挪过去,用手机光照着。
那确实是一张老旧的行军床,铁架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。床上苦布下盖着的,似乎是一床硬邦邦、黑乎乎的棉被,还有一个同样脏污的枕头。
难道……那个传闻是真的?真的有一个老兵,在这里潦草地度过了最后时光?
她的目光落在枕头旁边。那里,似乎放着一本深色的、厚厚的书。
她的手颤抖着,伸过去,拂开上面的灰尘和蛛网。
看清那本书的封面时,她的呼吸骤然停止!
是《普希金诗选》!不是她那一本,是另一本!版本更老,封面是深褐色的,同样破旧不堪!
她猛地拿起那本书,翻开封皮。
扉页上,用钢笔写着一个名字,字迹冷硬熟悉——陆沉戈。日期是:1965年。
这是他的书!早在她下乡之前,他就拥有这本书!
她疯狂地翻动着书页。里面同样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,笔迹更年轻,更锐利,但毫无疑问是他的!这些注解,比她那一本上的更加深入,更加个人化,甚至在一些诗句旁边,能看到他早年阅读时留下的、极其简短的感慨和疑问。
在这本更早的诗集里,他不是一个冷静的注解者,而是一个沉浸其中的、有着自己思考和波动的读者!
为什么?为什么他的书会在这里?在这个破败的、据说死过人的杂物间里?
一个更让她心惊的发现是,在书的最后几页空白处,不再有注解,而是反复写满了两个字,用一种近乎疯狂的、力透纸背的笔迹,写了一遍又一遍,覆盖了整页纸——
“代价”。
代价?什么代价?
林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,她背靠着冰冷的铁皮柜,滑坐到地上,大口喘息。手机光柱在她颤抖的手里晃动,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。
混乱的线索在她脑子里疯狂冲撞:辉煌的少将,潦倒的老兵,两本《普希金诗选》,未寄出的信,刻着名字的枪,还有这满纸疯狂的“代价”……
她猛地抬起头,目光再次投向那把锈死的柜锁。
她必须打开它!
她像是被注入了巨大的力量,站起身,在杂物堆里疯狂翻找。终于,找到了一根断掉的铁锹柄,一头还算尖锐。
她将锹柄尖端卡进锁环里,用尽全身力气撬动!
锈死的锁发出令人牙酸的“嘎吱”声,顽固地抵抗着。
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力,汗水混着灰尘从额头滑落,手臂酸麻,虎口被震得生疼。
“嘎嘣!”
一声脆响,锁环终于不堪重负,断裂开来!
林晚扔掉铁锹柄,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。她颤抖着手,抓住了冰凉的柜门把手,用力一拉!
柜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,被打开了。
一股更浓重的霉味和纸张特有的陈旧气味扑面而来。
手机光柱照进柜内。
里面没有她想象中的文件档案,而是……塞满了东西。
最上面,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、但依旧能看出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领章已经被拆掉。军装上面,放着一顶同样旧的军帽。
下面,是几本厚厚的、装订在一起的笔记,纸张泛黄得厉害。
旁边,有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物体。
最底下,似乎是一些散乱的信封和纸张。
林晚首先拿起了那几本厚厚的笔记。它们似乎不是工作日志,封面上没有标注。她翻开第一本。
第一页,只有一行字,日期是1977年冬。
“审查结束。结论:历史问题已查清,无现行问题。但鉴于边境事件指挥失当,造成不良影响,决定:免去现有职务,调离原单位,降职使用。”
林晚的手猛地一抖。
降职使用?1977年?那不是她离开后不久吗?边境事件?是指她报告的那次吗?指挥失当?
她急切地往下翻。
笔记里的字迹,不再是年轻时略带锐气的工整,也不是后期那种冷硬的平稳,而是变得时而潦草狂乱,时而虚弱颤抖,记录着他被审查、被边缘化、被下放到各个无关紧要岗位的过程。字里行间充满了压抑的痛苦、不甘的愤怒,以及……一种逐渐滋生的灰暗和绝望。
“……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失当?若当时反应慢半分,后果岂止‘不良影响’?” “……发配至农场后勤处,管理仓库。也好,图个清静。” “……旧伤时常发作,疼痛难忍。医药匮乏。” “……见到当年三连的人,调至此地任职,见我已形同陌路。世态炎凉,本该如此。” “……她应已毕业。很好。”
笔记断断续续,越往后,字迹越混乱,内容也越发灰暗。提到了几次重伤复发,无人照料,只能自己硬扛。提到了环境的艰苦,人心的势利。
最后一篇笔记,日期模糊,字迹几乎难以辨认,只有断断续续的词语:
“冷……”“药……没了……”“……不值得……”“……代价……”
笔记在这里戛然而止。
林晚浑身冰冷,如坠冰窟。
她明白了。“代价”。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!
因为那次边境事件?因为她的报告?还是因为……在评议会上力排众议维护了她,得罪了某些人?或者两者皆有之?
他后来的升迁呢?那个少将的身份呢?难道是……
她猛地拿起那些散乱的信封。大多是公函,调令,以及一些笔迹陌生的、措辞冷淡的回复信,关于他的病情复查、待遇问题等等。
直到她拿起一个没有任何署名的、泛黄的旧信封。
她抽出里面的信纸。
信纸是那种高级单位的专用信纸,抬头是一个她隐约听说过的、权限很高的部门名称。日期是九十年代初。
信的内容很短,措辞极其官方和冷硬。
“陆沉戈同志:经复核,你于XX年间所受处理确属不当,现予以撤销,恢复名誉。鉴于你身体状况及年龄,安排至XX干休所休养,享受相应待遇。”
没有道歉,没有解释,只有冷冰冰的“撤销”和“安排”。
在这封迟来了十几年的平反信下面,还压着一张小纸条。纸条上是陆沉戈自己的笔迹,只有一句话,写在那冰冷的公函末尾的空白处,墨迹深重,充满了讥诮和绝望——
“名誉?待遇?换我十几年蹉跎,一身伤病,值得吗?”
林晚再也支撑不住,瘫倒在地,泪水疯狂涌出,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!
他并非一路坦途升至高位。他曾跌落泥潭,在那漫长的十几年里,承受着不公、病痛和孤独,就在这样的地方,苟延残喘!而他最后得到的,只是一纸迟来的、毫无温度的平反书,和一个在干休所里等死的“待遇”!
那个少将的履历,恐怕只是最后几年恢复待遇后的一个虚衔。他人生最宝贵的年华,早已被碾碎在这残酷的命运车轮之下。
而她,对此一无所知。她在大学里憧憬未来时,他在被审查;她在工作中崭露头角时,他在管理仓库,旧伤复发;她结婚生子,享受家庭温暖时,他在这破屋里,写下满纸的“代价”和“不值得”!
巨大的愧疚和悲恸像山一样压下来,几乎将她碾碎。
她哭了很久,直到眼泪流干,只剩下干涩的刺痛和浑身彻骨的寒冷。
手机的光变得微弱,提醒她电量不足。
她挣扎着坐起来,目光落在那个用油布包裹的长条物体上。
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。
她伸出手,解开油布上已经失去弹性的绳子,一层层打开。
里面,不是枪。
是一把军工锹,锹头磨得锋利,木柄被手汗浸润得发亮。在木柄靠近铁锹头的地方,同样刻着两个字——
林晚。
日期也是:1969.冬。
和手枪上的刻字,如出一辙。
他不仅把她的名字刻在了武器上,也刻在了劳动的工具上。无论是在战场,还是在这片黑土地,她的名字,都与他融为了一体,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,无论荣辱,无论生死。
林晚紧紧抱着这把冰冷粗糙的军工锹,将脸埋在那同样冰冷的木柄上,终于发出了压抑不住的、绝望的呜咽声。
在这间破败、寒冷、弥漫着死亡和遗忘气息的旧屋里,在尘封的遗物和残酷的真相中,她终于触摸到了陆沉戈那沉默一生背后,全部的、惨烈的重量。
而这重量,几乎要将她彻底压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