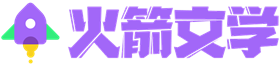梧桐巷的晨霜还没化尽,林未晞已经踩着薄冰走到老顾爷子的小院。朱漆院门虚掩着,门轴上的铜环挂着串干枯的梅枝,风一吹叮当作响,像串简陋的风铃。她攥着怀里的油纸包,里面是刚从陈婶那买的桂花糕,蒸腾的热气把纸包洇出深色的圆痕。
“丫头来得早。” 老顾爷子的声音从院里飘出来,混着劈柴的脆响。林未晞推门时,正看见老人蹲在石榴树下劈木柴,青布长衫的下摆沾着草屑,手里的斧头起落间,火星溅在结霜的地面上,瞬间就灭了。
“顾爷,借您的釉刷用用。” 林未晞把桂花糕放在石桌上,纸包的热气模糊了视线,“梅瓶该上釉了,我那几把新刷子总觉得不对劲。”
老顾爷子直起身捶了捶腰,晨光在他银白的胡须上镀了层金:“早给你备着呢。” 他转身往正屋走,拐杖在青石板上敲出笃笃的响,“那物件搁在樟木箱里快三十年了,昨儿沈小子来问起,我就知道你该来了。”
林未晞的心猛地一跳,跟在老人身后穿过月亮门。正屋的八仙桌上摆着只紫檀木盒,盒面的云纹已经磨得发亮,边角处刻着个极小的 “松” 字,笔锋苍劲,与祖父笔记上的签名如出一辙。
“打开看看。” 老顾爷子往紫砂壶里添了热水,水汽漫过他布满皱纹的脸,“这可是你祖父当年的心爱之物。”
林未晞的指尖在盒扣上顿了顿,黄铜的扣环带着经年的凉意。掀开盒盖的瞬间,股混合着樟木与松烟的气息扑面而来 —— 里面卧着把紫毫釉刷,笔杆是湘妃竹的,竹节处缠着圈褪色的蓝布条,刷毛细密得像层薄雾,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白。
“这是……” 她的指腹轻轻抚过刷毛,柔软得像婴儿的胎发,“祖父的釉刷?”
“当年你祖父修复那对哥窑贯耳瓶,用的就是它。” 老顾爷子往茶杯里倒着茶,琥珀色的茶汤在粗瓷杯里晃出涟漪,“那时他总说,好的釉刷得养,就像养壶,得用自己的手温焐着,刷毛才能记住釉料的脾气。”
林未晞忽然发现竹制笔杆上刻着行小字,凑近了才看清是 “民国二十三年春,赠砚农兄”。字迹比 “松” 字娟秀些,倒像是沈砚舟曾祖母的笔迹。她想起沈砚舟说过,两位祖父年轻时总以 “兄” 相称,原来不是客套,是真的亲如手足。
“这刷子有故事?” 她的指尖在 “砚农” 二字上轻轻蹭着,竹纹的凹凸感硌得指腹发麻。
老顾爷子呷了口茶,从樟木箱底层翻出个褪色的蓝布包:“你祖父和沈老先生闹翻那年,把这刷子留给了我。” 他解开布包时,手指有些抖,里面露出半张泛黄的契约,“这是他们合开窑厂时的分股文书,你看这里。”
契约上的墨迹已经发乌,却能看清 “林松年占股六成,沈砚农占股四成” 的字样。在 “备注” 一栏里,用朱笔写着 “若遇不可抗力,窑厂技艺归林氏所有,器物归属沈氏”,旁边盖着两个鲜红的印章,一个是 “松年堂”,一个是 “砚农斋”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 林未晞的声音有些涩,“他们早就料到会分开?”
“不是料到,是怕伤了和气。” 老顾爷子的拐杖在地上敲了敲,“那年头兵荒马乱的,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怎样。你祖父说,手艺不能断,物件不能散,就算人走不到一起,这两样总得留着念想。” 他忽然叹了口气,“可惜啊,后人只记得商场上的输赢,把这些念想全忘了。”
林未晞把釉刷放回木盒时,发现盒底垫着张极小的工尺谱,上面用毛笔写着半段《梅花三弄》的曲谱,音符旁标着些奇怪的符号,像窑温的刻度。“这是……”
“调釉的秘方。” 老顾爷子的眼睛亮了,“你祖父把釉料配比藏在曲谱里,‘工’对应石末,‘尺’对应釉果,这些符号是烧制的时辰。当年沈老先生总说他故弄玄虚,现在看来,倒是把真东西留下来了。”
回到铺子时,沈砚舟正站在柜台前翻祖父的修复笔记。晨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发间,侧脸的轮廓在书页上投下淡淡的影,像幅未干的水墨画。“顾爷把釉刷给你了?” 他抬头时,睫毛上还沾着点霜花。
林未晞把木盒放在他面前:“还藏着这个。” 她展开那张工尺谱,音符在晨光里像串跳跃的釉滴,“顾爷说这是调釉的秘方。”
沈砚舟的指尖在曲谱上轻轻点着,忽然笑了:“曾祖母的日记里夹着张一模一样的,她说当年祖父总对着这谱子发呆,以为是情书。”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个小瓷瓶,“这是按谱子配的釉料,老窑工说还差最后道工序。”
林未晞打开瓷瓶,釉料泛着淡淡的乳白,像稀释的牛乳。“得用松烟墨调。” 她想起工尺谱最后那个 “合” 字,旁边标着个墨滴的符号,“祖父说过,好的釉色得有‘骨’,松烟墨就是那点骨气。”
沈砚舟研磨松烟时,林未晞仔细打理着那把老釉刷。她用温水浸泡刷毛,看着它们慢慢舒展,像朵在水里绽放的墨莲。忽然发现刷毛根部缠着根极细的红线,抽出来时带出张小纸片,上面用铅笔写着 “三月初三,窑温千二”。
“这是烧制梅瓶的日子。” 沈砚舟的指尖在纸片上轻轻拂过,“曾祖母的日记里写着,那天晞如姑娘偷偷来看窑,你祖父特意把窑温提高了两百度,说要让釉色像她的胭脂。”
林未晞的心跳漏了一拍,往釉料里加松烟墨的手有些抖。墨汁在乳白的釉料里慢慢晕开,像朵在水里盛开的墨花。“原来他们……”
“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。” 沈砚舟的声音低了些,“曾祖母说,晞如姑娘那天戴了支梅花簪,你祖父就把梅枝画进了瓷瓶。他们都在等,等一个不可能的将来。”
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铺子,林未晞开始给梅瓶上釉。老釉刷在她手里格外听话,刷毛蘸着调好的釉料,在瓷片上轻轻拂过,留下层均匀的薄膜,像晨雾落在花瓣上。
“得顺着釉面的开片刷。” 她教沈砚舟握笔的姿势,掌心贴着他的手背,“你看这开片像不像渔网?得跟着网眼走,不然釉料会积在缝隙里。”
沈砚舟的呼吸拂过她的耳畔,带着点松烟墨的清冽:“这样?” 他的手腕轻轻转动,釉刷在梅瓶腹部画出道流畅的弧线,正好避开了那道隐藏的接痕。
林未晞的脸颊忽然发烫,松开手时,看见陈叔正趴在门口的梧桐树上偷看,见她望过来,慌忙装作摘叶子。“陈叔进来喝杯茶啊!”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,撞倒了案上的朱砂碟。
红痕溅在沈砚舟的米白色衬衫上,像朵突然绽放的红梅。他却没在意,只是捡起瓷碟笑道:“看来这梅瓶还得沾点红才像样。” 他用指尖蘸了点朱砂,在她刚刷好的釉面上轻轻点了点,“就当是给老物件留个新念想。”
傍晚收摊时,老顾爷子拄着拐杖来了。他看着案上的梅瓶半成品,忽然指着底部的圈足:“这里少了道弦纹。” 老人的指尖在圈足上比划着,“你祖父当年修东西,总爱在圈足加道细弦,说是‘画龙点睛’。”
林未晞忽然想起那对青花碗的碎片,圈足处果然有圈极细的弦纹,以前总以为是自然形成的。“这也是种记号?”
“是念想。” 老顾爷子的拐杖在地上敲了敲,“就像沈老先生总在器物底款加个小点儿,你们现在修这梅瓶,不也在偷偷留记号?” 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转了圈,忽然笑了,“当年你祖父把釉刷留给我时说,‘总有一天,会有两个年轻人拿着半只梅瓶来找它’,看来他没说错。”
月亮爬上屋脊时,林未晞把上好釉的梅瓶碎片放进特制的干燥箱。沈砚舟往箱底铺着干燥的宣纸,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,像两滴相融的釉料。“明天就能进窑了。”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铺子里格外清晰,“老窑工说,得烧整整一夜。”
林未晞点了点头,看着干燥箱里的梅瓶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乳白。她忽然觉得,这八十多年的时光像场漫长的窑火,把两家的恩怨烧成了灰烬,却把那些藏在釉色里的念想烧得愈发纯粹。
离开铺子时,沈砚舟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小锦盒:“祖母让我给你的。” 里面是枚银质书签,上面刻着极小的梅枝,枝桠间藏着个 “晞” 字,“她说这是当年晞如姑娘的嫁妆,辗转落到沈家,现在该还给林家了。”
林未晞捏着书签的指尖微微发颤,银质的凉意里仿佛还带着胭脂的甜香。“谢谢。” 她把书签夹进祖父的笔记里,正好是那页写着 “匠心即诚心” 的地方。
巷口的馄饨摊还冒着热气,林未晞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沈砚舟的车消失在雾里。汤碗里的葱花在热气里翻滚,像片小小的绿云。她忽然想起老顾爷子说的 “器物会认主”,或许不是器物认主,是那些藏在釉色里的念想,总会找到懂它的人。
回到铺子后,林未晞把那把老釉刷小心地放进紫檀木盒。月光透过窗棂照在盒盖上,“松” 字的刻痕里像落满了星星。她知道,明天进窑的不只是半只梅瓶,还有两段被时光掩埋的往事,和两颗正在慢慢靠近的心。
窗外的风卷起最后几片枯叶,落在积霜的青石板上。林未晞铺开宣纸,在月光下写下 “窑火” 二字,笔锋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她忽然明白,祖父留下的不只是门手艺,更是种勇气 —— 敢于修复裂痕的勇气,敢于原谅过往的勇气,敢于在灰烬里重新开花的勇气。
工尺谱上的《梅花三弄》仿佛在耳边响起,音符里混着窑火的噼啪声,混着两位祖父的笑声,混着晞如姑娘轻嗅梅花的呼吸。这些声音穿过漫长的时光,在这间小小的铺子里交织成温暖的河,带着她和沈砚舟的脚步,慢慢流向即将到来的黎明。